【荒謬如果有顏色,我想是綠色的】---陳水扁總統前的飛彈、村上春樹的肯德基上校、李安的比利林恩,還有忍者龜。

荒謬如果有顏色的話,我想是綠色的。
兩千零六年的漢光演習,有一顆拖式飛彈掉到距離總統陳水扁面前,一百多米處的海面上爆炸。當天媒體的新聞標題是:「拖式導彈射偏,險些要了阿扁的命。」
然而這顆,長達一點多公尺的飛彈,是我裝填的。
而我就坐在那一台發射飛彈的履帶式裝甲車裡面,在甲板上摀著耳朵。
這是第一個演習階段,我與同袍是座落在宜蘭海灘上的反裝甲部隊,甲車的壕溝與掩體,是我們花了兩個月構工,用一支支鐵鏟、加上一袋袋沙袋,甚至外加學弟被太陽曝曬而造成的二級灼傷,給清理構築出來的。目的是對付海面上遠距離進犯的水陸戰車,再模擬應對殘餘的敵軍搶灘。
由於是實彈演習,只能有志願役士官操作,在士官長發射飛彈後,我們的副排長,必須操作五零機槍,在海灘上掃射假想敵。一顆顆發燙的機槍彈殼,灑落在我的鋼盔和綠色迷彩服上。
隨著媒體報導,國軍瞬間變成國際笑柄。但沒有人知道,這是一顆1999年向美國購買回來的拖式飛彈,據說是三十多歲的「老飛彈」。演習,是將老飛彈除役的最好藉口。
但是,為何我國要花錢購買「高齡」飛彈,然後再從演習中「退役」。
為了這一場演習,我們花了兩個多月,駐軍在小學、睡在學校圖書館、每天搬運重達數十公斤的各式武器,並於六月多的溽暑,在鹹水味的宜蘭海邊挖砂、堆沙包、搬發電機、埋軍用電話線,晚上三人擠在一間淋浴間洗澡、每天站凌晨兩點到四點的夜哨,保護置放在郊外的甲車,拎著步槍、躲在甲車裡面邊打瞌睡、邊看滿天的星星,結果只換取一則笑話。
還有換來累積兩個多月帶回營區的垃圾,以及垃圾裡面被便當廚餘養大的,小拇指大小的蛆。
同校的朋友曾說過,他服役時,寢室鬧鼠患,老鼠會跑來吃置物櫃裡面的乾糧,分隊長被上級下達一個指令,必須每個禮拜抓到三隻老鼠,往上呈報。但是老鼠不好抓,只會愈抓愈少,分隊長索性就把第一個禮拜抓到的三隻老鼠,養起來,每當往上呈報時,他就拿那三隻老鼠交差,三隻老鼠,被養得胖胖的,相當可愛。

這故事讓我突然回想到,我藏在置物櫃上方、鋼盔底下的那本《海邊的卡夫卡》。二十歲那時,在漢光演習之前,我在苗栗受訓,被部隊要求受兩噸半手排輪車的駕駛訓練,但我感到相當挫折,入伍前剛拿到駕照,根本沒有開過自排車,還會一隻腳踩煞車,一隻腳點油門,卻居然通過考試。
拿到駕照後開始擔任駕駛,因為看錯指揮手勢、開著兩噸半、大約垃圾車大小的輪車,差點把排長撞飛。進入基地訓練、開著悍馬車探戰車砲靶時,一個迴轉,就把悍馬車的保險桿撞成九十度的「七」字型。我的學長只好邊罵髒話,邊幫我收拾殘局,一邊用電動圓鋸鋸開折彎的保險桿,再折回原本的角度,然後再焊接起來。
這些軍中的痛苦經驗,導致於我企圖從現實中的荒謬,逃避到虛構中的荒謬。
當時我期許自己,能夠擁有小說裡面的男主角,十五歲的田村卡夫卡,一個人離家出走所具備的堅強。
但是當小說裡,肯德基上校突然跑出來說話時,我還是傻眼了,是的,就是白色頭髮、黑色眼鏡的肯德基(桑德斯)上校。
而且賣的不是炸雞,拉的卻是皮條。
是一個沒事會跑過來跟你說:「我可以為你提供最棒的性愛機器喔。」的肯德基上校。
二十歲的我,並無法理解為何村上先生要選擇這些符號和隱喻,作為包裝故事的形式。
直到多年後我讀了《發條鳥年代記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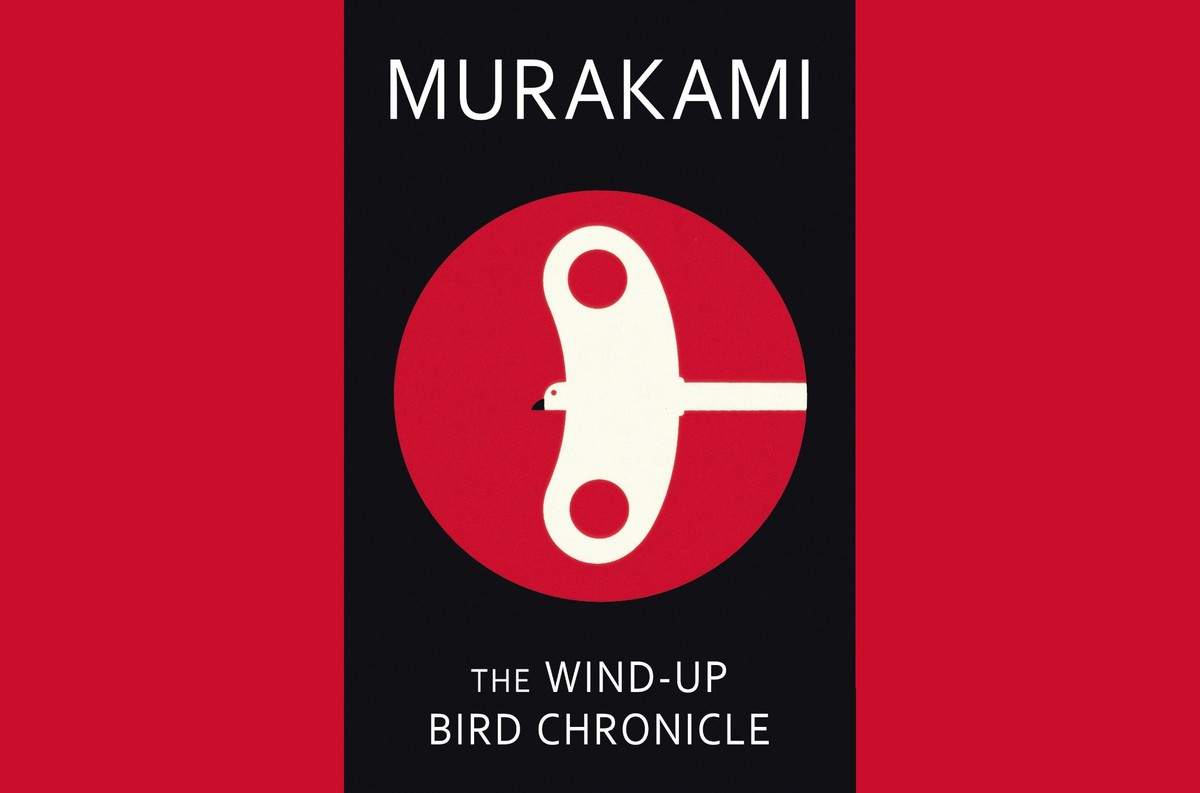
《發條鳥年代記》裡,描述諾門罕戰役中,有一位中國裔的、滿州國軍士官校的學生,企圖逃出日本人的掌控。中國學生拿著一支球棒,打死了兩名日本教官。於是上級交付了一個任務給日本籍中尉,給了他一支球棒,要求用相同的方式,打死那一個殺人的中國學生。
中尉將伍長叫來,教導他如何用最俐落的揮棒手法,球棒往後舉、下半身扭轉回來,讓身體迴轉。只為了讓那一個中國學生,以不受痛苦、最迅速致命的方式死去。
這一棒,把我打醒。
這一棒,幫助我看懂村上春樹先生的小說,以及關於體制性暴力所製造出的荒謬。
這一棒,甚至幫我找到村上先生,與李安先生作品的共通點。
他們要共同對抗「荒謬的惡意」。

《臥虎藏龍》裡的李慕白,礙於禮教,所以只能在中了碧血狐狸的毒針、將死之際,才敢向俞秀蓮傾訴愛意。
李慕白殺人,居然比愛人容易。

《色戒》裡,暗戀王佳芝的鄺裕民,為了民族大義,可以讓自己心愛的女孩,與唯一有性經驗的同學梁潤生發生關係,只為了練習色誘他們亟欲暗殺的目標,汪精衛的情報頭子,易先生。鄺裕民有勇氣殺死知道實情,前來勒索的老曹,卻沒有勇氣保護王佳芝。
鄺裕民和易先生原來一個樣,殺人,居然比愛人容易。

《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》裡,為了拯救陷入埋伏的長官,比利林恩衝進槍林彈雨的前線,將長官拖進壕溝掩護,並與前來殺敵的伊拉克敵軍進身肉搏。此勇敢的舉動全程被攝影機拍下,讓比利林恩變成貨真價實的美國英雄。
回到美國的比利,所遭遇的,卻是其他試圖將英雄價值,化作產值的商人,他們將比利林恩變成一種捍衛美國價值的觀念、變成一場球賽的中場商演、一筆電影授權的交易。比利最後寧可離開他心愛的女孩與姊姊,選擇回去戰場,為保護他所愛的同袍弟兄們,準備殺死敵人、也給敵人殺死他的機會。
比起李慕白、鄺裕民、易先生,比利林恩陷入更荒謬且悲傷的情境,他並不是選擇殺人,比愛人容易。
而是比利林恩,選擇用殺人,來證明他愛人。
比利林恩完全應驗了村上先生,在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裡頭所書寫的一句話:「……我說的你懂嗎?人不是因為缺點,而是因為美德而被拖進更大的悲劇裡去的。」
我突然理解,村上先生,為甚麼要使用拉皮條的肯德基上校,當作故事裡面的角色了。

村上先生企圖用虛構的荒謬,來對抗人們已經習以為常,卻不企圖反抗的,現實的荒謬。就好比忍者龜,為什麼人們會期待四隻壯碩的綠色烏龜,打敗腦袋外露的外星人,拯救人類呢?並且用巨額的資金,將牠們製作成動畫、拍攝成電影,找四個大男人,來扮演烏龜呢?
如果烏龜都可以學會忍術、拯救世界,那肯德基上校,為甚麼不能拉皮條呢?
如果你不能接受拉皮條的肯德基上校、不能接受拯救世界的忍者龜,那為什麼你能夠接受,在現實之中,人類被殺死,卻被當作習以為常的荒謬呢?比起殺死人類的惡意荒謬,忍者龜的荒謬,甚至是善意的。
因為牠起碼為孩子帶來歡笑。
比起質疑忍者龜的荒謬,你勇敢對抗現實的,充滿惡意的荒謬嗎?
卡繆曾說,遇到荒謬而不抵抗,才是真正的荒謬。
村上先生和李安先生,勇敢地用虛構的故事與現實對抗。
最後請允許我引用,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,斯維拉娜‧亞歷塞維奇,在她的紀實文學《我還是想你,媽媽》的引言。
她這麼說:「杜斯妥也夫斯基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:如果為了和平、我們的幸福、永恆的和諧,為了它們基礎的牢固,需要無辜的孩子留下哪怕僅僅一滴淚水,我們是否能為此找到一個充分的理由?
他自己回答到:這一滴淚水不能宣告任何進步、任何一場革命,甚至於一次戰爭的無罪。它們永遠都抵不上一滴淚水。」
戰爭會為孩子帶來淚水,但是忍者龜不會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